十月的黃河裹挾著賀蘭山的碎金奔涌向前,我站在魯家窯水庫的堤岸上,望著遠(yuǎn)處青灰色的泵站建筑群���。那些棱角分明的混凝土結(jié)構(gòu)在晨霧中若隱若現(xiàn)�,像極了一排守護(hù)河套平原的哨兵。十年前���,這里還是一片荒灘�,如今已是自治區(qū)現(xiàn)代化水廠示范點�。作為寧國運(yùn)集團(tuán)的一名老員工,我親眼見證了這片土地的滄桑巨變����,也親身經(jīng)歷了寧國運(yùn)這十年的跨越式發(fā)展。
那時的魯家窯水庫還泛著堿白的泡沫��,像條病懨懨的銀鏈蜷縮在戈壁灘上���。泵站值班室里���,泛黃的《黨員學(xué)習(xí)手冊》在春風(fēng)中簌簌翻頁,封面上“寧國運(yùn)”三個燙金字被歲月磨得發(fā)亮���。如今翻閱當(dāng)年的工作筆記����,扉頁上歪歪扭扭抄著時任黨委書記的講話:“要讓每一滴水都折射出黨的光輝”�。這句話,竟成了我們十年跋涉的注腳�����。
十年前的寧國運(yùn)����,還是一家傳統(tǒng)的區(qū)域性企業(yè),面臨著資源枯竭��、市場萎縮的雙重壓力��。記得第一次參加職工代表大會時�,董事長擲地有聲地說:“我們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(jìn)改革,以創(chuàng)新驅(qū)動引領(lǐng)轉(zhuǎn)型發(fā)展����!”這句話,像一記重錘����,敲醒了在場每一個人����。
改革的路從來不會一帆風(fēng)順����。推進(jìn)混合所有制改革時,一些老職工不理解���,擔(dān)心自己的“鐵飯碗”保不住���。黨委班子帶頭深入基層���,與職工面對面談心�,講政策、算細(xì)賬�����、謀出路���。宣傳干事們編印了上千份宣傳手冊���,組織了幾十場宣講會���。漸漸地,職工們的思想通了��,改革順利推進(jìn)��。如今���,我們的混合所有制企業(yè)已經(jīng)成為寧國運(yùn)集團(tuán)新的利潤增長點。
2016年深冬的某個夜晚�����,紅寺堡水廠的值班室燈火通明�。我裹著褪色的工裝棉襖,盯著屏幕上跳動的壓力曲線�,值班室鐵皮爐子里烤土豆的焦香混著柴油味。那時我剛調(diào)到維修隊�,跟著師傅維護(hù)保養(yǎng)20世紀(jì)90年代的老舊管網(wǎng),常要頂著零下二十?dāng)z氏度的嚴(yán)寒搶修凍裂的水管�����。記得有次在大河鄉(xiāng)搶修管道,老鄉(xiāng)把自家熱炕讓給我們暖身子�����,桌子上擺著夏天摘回來的枸杞���,鮮紅香甜����。
轉(zhuǎn)機(jī)出現(xiàn)在那個飄著柳絮的春天�。水投集團(tuán)黨委會議室里,“黨建引領(lǐng)智慧水務(wù)”的紅色橫幅映著每個人的臉龐�。這是我第一次聽說“城鄉(xiāng)供水一體化”這個陌生詞匯,看著大屏幕上三維管網(wǎng)模型像血管般在寧夏地圖上延伸�����??偣こ處燀斨ò最^發(fā)站起來:“咱們這把老骨頭,也該學(xué)著用用新式武器了”��。
三年后的立夏�,我來到柳泉鄉(xiāng)安裝首批智能水表。烈日下,回漢鄉(xiāng)親們捧著蓋碗茶守在場院����,看我們把巴掌大的電子設(shè)備嵌進(jìn)水泥表井。有位回族老大爺顫巍巍撩起湯瓶洗手���,清水濺在銅表盤上折射出七彩虹光:“這小東西靈得很嘛�����,裝上這個我們就再也不用月月下井子查水表了?��!蹦翘焓展r晚霞似火��,我看見同事們蹲在田埂上教農(nóng)戶用手機(jī)查用水量�,工裝后背洇出的汗?jié)n像幅水墨山水��。
在羅山腳下的新莊集鄉(xiāng)��,我們鋪設(shè)的滴灌管網(wǎng)正孕育著奇跡�����。一個叫馬燕的回族媳婦領(lǐng)著我看她家的枸杞田,暗紅色枝條下埋著黑色輸水管�����?!耙郧皾菜矿H馱,現(xiàn)在手機(jī)能遙控���?����!彼闷痤^巾擦汗�,陽光穿過智能噴頭的水霧���,在她鬢角凝成細(xì)小的彩虹���,更遠(yuǎn)處的揚(yáng)水泵站將黃河水送到千家萬戶的田間地頭。
2020年中秋的月�����,照著魯家窯水廠新建的二期凈水車間格外明亮���,80后技術(shù)員李工正調(diào)試從國外引進(jìn)的凈水設(shè)備�。他的工位上貼著一張泛黃的全家福,父母在固原山區(qū)那孔窯洞前笑得靦腆����。“小時候爸媽帶著我和哥哥姐姐每天走六里山路背水���,誰能想到現(xiàn)在回家�,水龍頭一擰就能喝到清澈的黃河水�。”他說著忽然紅了眼眶�����,“可惜爺爺沒等到……”控制臺藍(lán)光閃爍��,玻璃幕墻外�,輸水管正將清泉送往千溝萬壑����。
轉(zhuǎn)眼2022年���,9月中寧縣疫情突至�����,紅寺堡區(qū)弘德村作為隔離點���,里面住著所有密接者和近萬名居民,凌晨一點��,園區(qū)突然水壓不足情況��,紅寺堡水務(wù)公司班子成員立刻齊刷刷開啟攝像頭�,指揮維修人員連夜開展搶修,大家團(tuán)結(jié)一心��、齊心協(xié)力��,經(jīng)過3個多小時的奮戰(zhàn)��,順利完成搶修任務(wù)����,早晨6點隔離點和居民用水水壓恢復(fù)正常。天還沒亮��,十二支黨員先鋒隊的紅馬甲已然穿梭在大街小巷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我們調(diào)試完最后一處管道水壓,晨光中飄來面點鋪蒸籠揭開的霧氣�,那縷人間煙火氣,竟比任何捷報都令人眼眶發(fā)熱�����。
去年深秋����,我隨調(diào)研組探訪“十二五”生態(tài)移民村弘德村。嶄新的文化廣場上��,幾位老人圍坐在直飲水機(jī)旁下象棋�����,水流聲混著枸杞蜜的甜香��。村支書指著遠(yuǎn)處的魯家窯水庫說:“有了黃河水����,娃娃們再不用喝苦咸水了����?�!蹦荷?���,家家戶戶的炊煙與輸水管道的白霧交織�,繪出塞上江南的新水墨。
十年間�,辦公室窗外的白楊又添了十圈年輪。工資條上的數(shù)字悄悄上漲�����,職工書屋的燈光愈發(fā)明亮�����,文體中心的羽毛球場上���,退休老書記還能打出漂亮的扣殺���。前不久,新入職的畢業(yè)生指著黨員活動室墻上的老照片問:“師傅�,這照片里拿鐵鍬的是您嗎�����?”我抬頭瞥見自己鬢角的白發(fā)��,忽然想起十年前老班長的那捧黃河水——原來我們真的把自己澆灌進(jìn)了這片土地�。
十年長卷在記憶中徐徐展開:紅寺堡揚(yáng)水工程竣工時震天的花兒漫唱�,清水河治理后重現(xiàn)的蓑羽鶴,智能化調(diào)度中心那些跳躍的綠色數(shù)據(jù)……它們?nèi)缤S河浪尖的晨星�,照亮了每位職工額頭的皺紋與白發(fā)。那些被汗水浸透的黨徽����,那些磨破又補(bǔ)丁的工作服,那些永遠(yuǎn)帶著水漬的工程圖紙���,都化作長堤的基石��,托起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渴望���。
十年風(fēng)雨兼程,十年春華秋實�����。作為寧國運(yùn)發(fā)展的參與者��、見證者���,我深感自豪�。站在新的起點上�,我將繼續(xù)以奮斗者的姿態(tài)�����,與寧國運(yùn)同呼吸、共命運(yùn)�����,為譜寫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新篇章貢獻(xiàn)自己的力量�����。
眺望著遠(yuǎn)處繁忙的車站����,一列列滿載希望的列車正駛向遠(yuǎn)方。這十年,寧國運(yùn)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���,載著全體職工的夢想�,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��。而我���,很榮幸成為這列車上的一員�����,與它一起����,駛過風(fēng)雨���,駛向彩虹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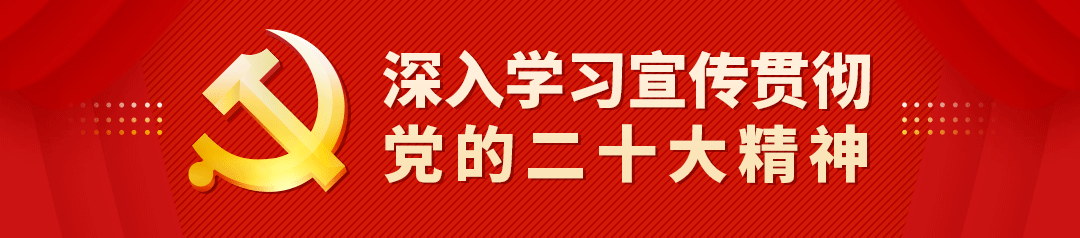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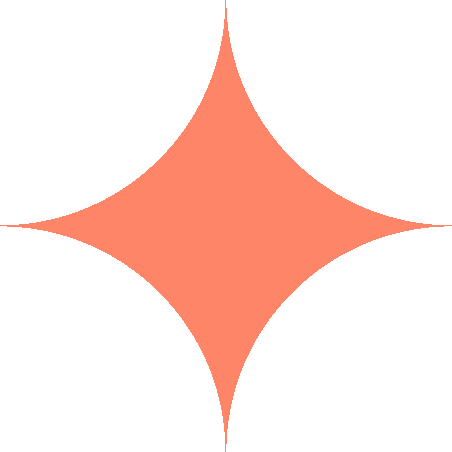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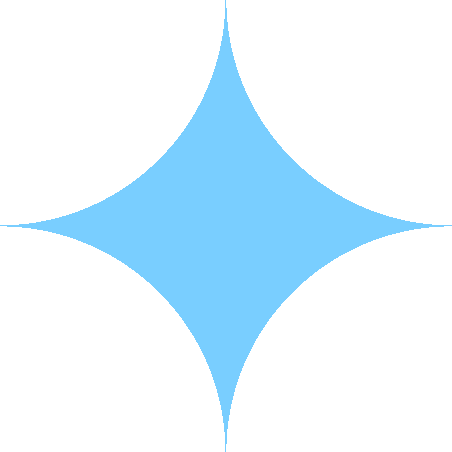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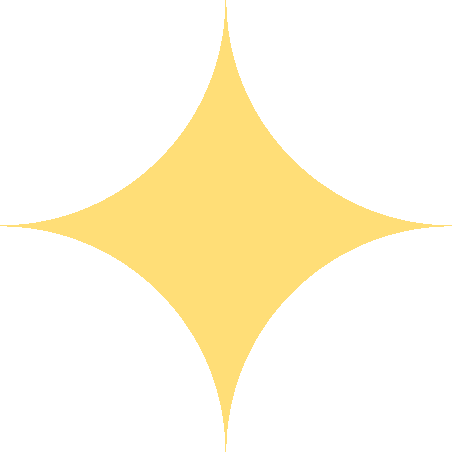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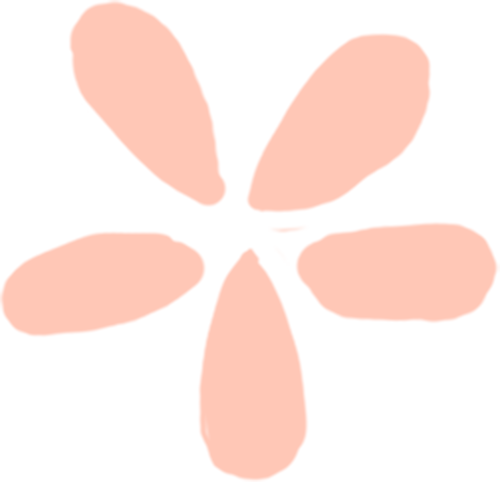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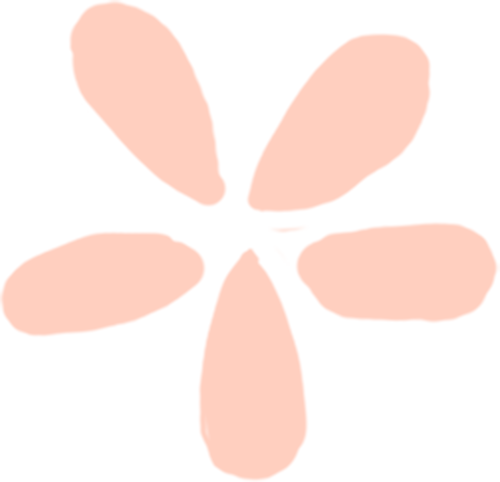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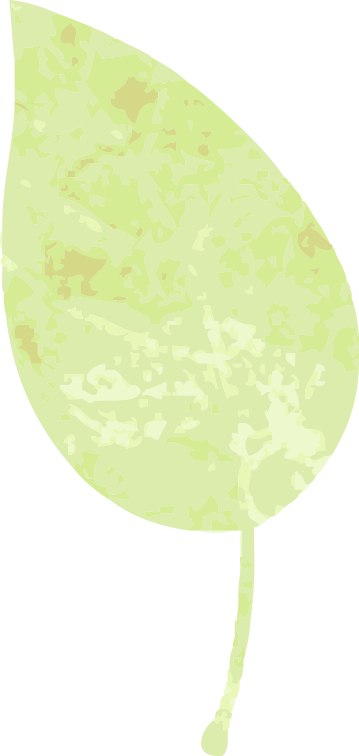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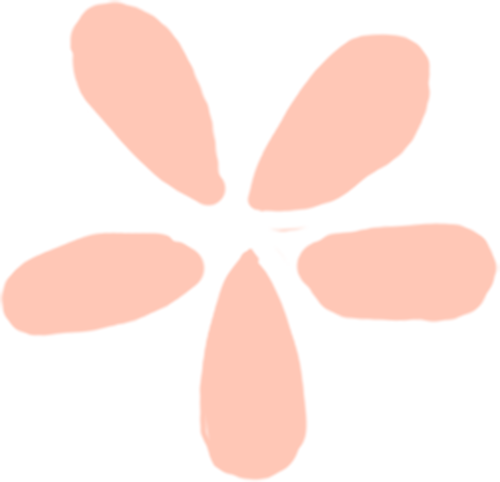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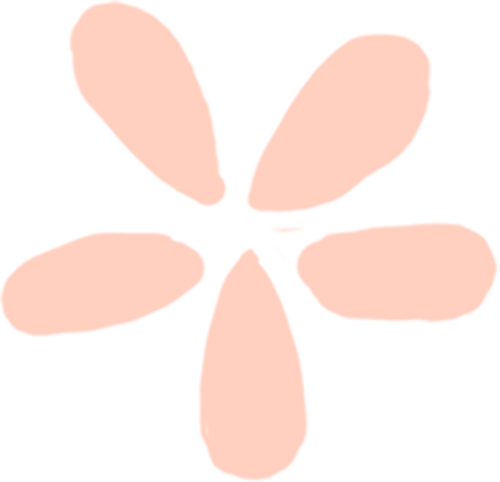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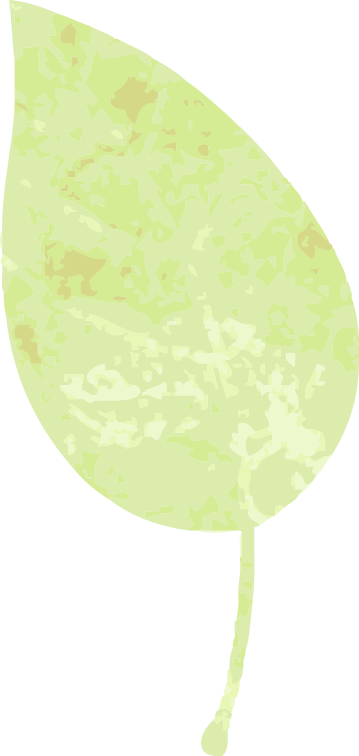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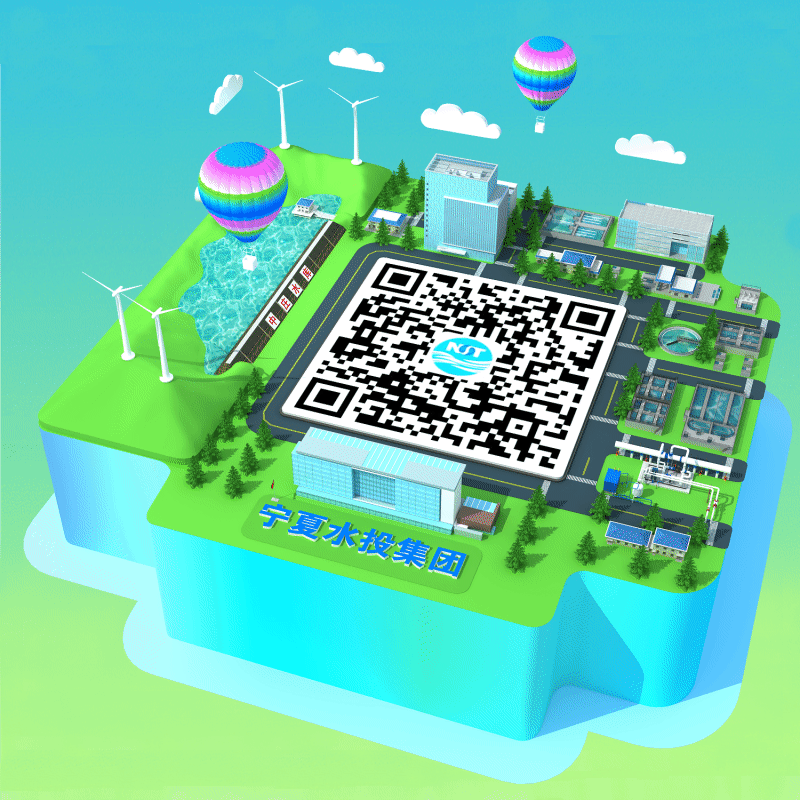



 企業(yè)網(wǎng)群
企業(yè)網(wǎng)群

